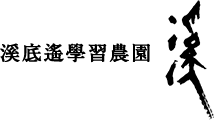文/馮小非
下午四點鐘,村子裡的龍眼市場聚著一群老農,站著的人端正,坐著的肅靜,彷彿為了什麼重要的理由,正要隆重的拍下一張紀念照。這樣的姿態維持了好久,始終沒聽見攝影師喊卡的聲音,倒是有人累了,換個姿勢站坐,轉身也不忘將眼睛定在看的見大路的位置,好像一不注意,就要錯過了重要的畫面。
市場上的鐵棚遮住了太陽,棚內已無光陰,直到那台藍色小貨車開進方場,驚動了場外的一群鵝仔,它們引吭嚎叫,搖晃著身軀前後繞圈,如鐘擺重新啟動了時間。農人停止凝望,起身投入日常。
貨車上跳下來幾名男人,拿出磅秤立於場中,農人將各自的簍子搬來,以秤為中心繞成前後兩排圓形,輪到過磅的就出力上陣,還沒輪及的且將雙手抱於胸前,盯著販仔動作。主事者拿著筆和一本簿子,當磅秤的指針停止最後振動,旁人報出斤兩,他持筆記下數字,如交通警察撕給農人一聯黃單,單一離手,農人將龍眼抬下,換下一位上場。
當農人逐漸由外圍接近磅秤,被秤過斤兩的農人形成另一列隊伍,要將自己簍子裡的龍眼裝入販仔帶來的籃子。後面的農人緊張的看著前人的動作,不時喚著,壓卡實咧!每當一個籃子裝滿要交出去,他們便喊著,裝卡滿啦!還沒過磅的農人不時轉頭,瞇著眼,注意空籃子消失的速度。
終於所有的龍眼都裝進販仔帶來的籃子裡,早先從貨車上跳下的男人們又跳回車上,要將這些龍眼疊好離場,農人們拿著黃單,再度圍繞著剛才開單的販仔頭,現在他手上多了一台計算機,照排隊算錢。你─279斤,1395元。你─250斤,1250元。你─……。
領過錢的農人往旁邊走兩步,鈔票塞進褲子的口袋,手裡仍拿著那張單子,楞楞的看著,一遍,再一遍,好像還有更多的數字,藏在單子上的某個角落,需要用力的注視才會顯現。終於看到一個程度,確定這樣努力應是無望,願意將單子塞進胸前的口袋,且掏出一支煙來吐氣。
隨著答案一個個揭曉,農人們往外走去,又不約而同的繞著貨車周圍,看販仔疊貨。你多少?1395。阮也是。拿單子出來比看,你幾個人摘?對方比出勝利的手勢,同款,阮也是尪某兩個,今年一葩就生很多,不用爬到樹頭,若不是販仔有限定,只這些?說實在,今年龍眼真正沒話講,甜又大粒,但是想到賣不出去,心肝就起懊惱,想要做就腳軟,一天落眠床固定要多少錢開銷,5元是算什麼價錢?
那還是拜託的咧!今年根本就無販仔來收,交文市的一斤才6元,去年壞壞還有10元,你看今年這樣,再兩禮拜,我看4元都有可能。今日這是阿義打電話去叫的,他們要做龍眼乾,才答應進來,還沒要收多少哩,昨天就特別吩咐,載多少籃子來就載多少,你沒看大家緊張的,要是裝不進去,看賣去給誰?
真正都市人都不愛吃龍眼?伊們現在選擇很多,都要吃了可以減肥的,嫌龍眼太甜,不健康。你沒看今年荔枝也是,5元!6元!幹哩…..,都叫來做山,一日就瘦下來!不可能啦,龍眼山多斜,你沒聽人說咱這「放屎未著」,連放一坨屎都留不住,看有多斜……。
眾人嚷起笑聲,一邊閃躲貨車發動引擎的廢氣,四散到龍眼市集的角落。販仔要走了,大家看阿義,伊站在路旁,跟車上的人不知在交涉什麼,車子油門催著催著,阿義幾乎跟著小跑步,終於攔不住,拍拍車門,放車離去。貨車一彎出路口,人們又從四處聚攏過來。阿義,明日….我幾點來卡好?隨人自由啊,反正販仔無要來。
下午五點鐘,村子裡的龍眼市場聚著一群老農,喫煙的人互相點火,說話的人興致高昂,從選情說到昨天開的大家樂,彷彿為了什麼理由,正要進行一場盛大的宴會。這樣的情形維持了好久,沒再聽見一字與龍眼有關的話語,若不是場外掛著招牌,一不注意就要忘記,這是一個龍眼的市集。
【後記】
2002年的8月,我寫過一篇關於龍眼的文章,那時的價錢約8至12元,已極為接近成本。今年在相同的月份,產地只有一斤6至8元的行情。那天經過村子裡的龍眼市場,看見一群老農直定定的坐著,等待販仔來收龍眼,一斤只有5元。
「龍眼的外殼就像人的臉,隨著成熟度會留下歲月的刻痕,沒有梨子光滑,也沒有蘋果紅潤,老東西也許只能與老朋友分享,所以種龍眼的人越來越老,吃龍眼的人年紀也越來越大了….」,這是我去年寫過的話,今年我多了一歲,龍眼價格也跌了一半。
我的同事畫了一幅阿婆撿龍眼的景象,我也希望將來變成阿婆的時候,山上還有很多龍眼樹,樹上的留著賣錢,樹下的讓我一路走一路撿,從七夕吃到團圓,再留一些焙作乾,冬天來煮桂圓茶;來春龍眼花開,向鄰居買幾罐純良的龍眼蜜滋潤心肺,若是避過鬼門關,再撿一路的龍眼。
(本文刊登於「青芽兒雜誌」第四期)